等我
时间:2011-10-17 00:19来源: 作者:青空青沙 点击:
次
我似乎有些明白,或者不明白,在铃同我说那句话时。
就像汽车碾过铺陈在马路上的稻谷时,疼的不仅仅是稻谷。十八岁的天空有着漂浮的白云,也有着飞机划过的尾翼。青涩的果实往往没有表面那么可口。
原以为会像许多在中国教育制度下平淡无奇地掠过高中,而后又潇洒地过上选修课必逃,必修课选逃的大学生活。
但一切的平静,在认识宇的那年夏天开始——
认识宇是源于偶然,但谁又知晓偶然不是源于自然。又或者假装深沉地说,有缘注定相见。宇是我们学校的家常。因为在众星拱月下,很荣幸,他不知不觉得到了校草的头衔。用他对我说的一句话说,就是“我简直是他们握在手中玩弄的布偶”。是有些偏激。不过,或许真有这么夸张,因为就连他在宿舍穿什么样的内裤都曾一度在校园里传得沸沸扬扬。人也许怕出名,不然高琨也不会让一次诺贝尔奖搞得鸡犬不宁;泰戈尔也不会因此远离芒果树下的天堂。
或许就像铃疯狂地以宇为偶像一样,我也在悄然中获得了学校的病毒。篮球场上,宇潇洒地身影尝尝是占据我的眼眶的。但那时我和宇也只是我从楼梯上,他从楼梯下的关系。是那几次的偶然使我们的关系改变。高二那年的夏天,命运似乎有意牵扯我们。打羽毛球时,我撞到他,他礼貌地笑了笑;打篮球时,篮球打到他,他礼貌地笑了笑;下楼梯时,撞到他,他一把扶住我,向我说了一句话“小姐,你和我有仇啊”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命运让他闯进我的生命?不过,我从未细想过高中生活没有他,是不是乏善可陈?
没有像有些恋人的一见钟情,我和宇也被编排到了慢热型的队伍中。宇常常说:“青春的年龄经不起时间的流逝”。他怕,我们的关系也会随着海水在净化器中淡化。我只能莞尔一笑。这一笑潜藏着太多的情绪,是无奈?是不以为然?是害怕?就像我无法回答一个孩子卡布奇诺为什么比一般的咖啡甜。
同宇交往的日子,我们重复着一般恋人的步骤。看电影,夜市。很多人常说90后的青春喜欢标新立异,殊不知90后的我们正喘息在“应该”中。
我或许是一种淡定的人,就像地快坍塌了,我还能在八楼上从容不迫地拿起手机说:“好,我马上下。”我不知道这样的性格是谁造就的,因为看过我爸妈为我中考的报名急的团团转的样子,你就会说:“你简直不是你爸妈生的。”也许吧!宇常常抱着我说:“你好轻。真怕你从我怀里逃走。‘其实不是这样的,因为,我也会怕。地板破裂了,碾碎的是我的肉体,而宇的离去将是撕裂我的心。
宇能荣登校草的宝座,绝不可能是无稽之谈。铃常说:“如果宇上快乐男声的话,岂会有陈楚生得第一的机会。宇是一个天之骄子。不仅篮球打得好,歌也唱得很好。他是星二代,他妈妈曾经是红遍大江南北的民歌歌手。许是良好的基因使他唱歌唱得很好。但对于像他这种通过音乐升学的学生来说,没有一番努力是不行的。星期一、星期三的下午我陪他练歌;星期二、星期五的下午我陪他打篮球;星期四的下午他陪我写作。像我这种平凡长相的女生,学校理科生的拖油瓶能够扯上宇简直就像是童话。可是并不是所有的灰姑娘都能如安徒生的陈述那样——过上幸福的生活。
我不知道我同意宇的离去是对这段感情的终点,还是给青春的遗憾,一种错觉,希冀他能带着他的梦想同我环游到南美洲的仙境瀑布。我曾说宇的离去会让我想脱了线的风筝,茫然无措。但真正遇到时,我还是坦然地去面对现实。
那段时间,宇常常是欲言又止,这让我很不习惯,对于一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来说,宇的行为让我感到不安。可是我不会主动去捅破这层纸,在他的心理准备还未完整的时候,我贸然地跨越会让他退缩。终于,在哪一个晚来的台风的日子,在艺术楼镂空的楼底,他说了:“我妈要我到巴黎。”我不知道是不是暴雨冲刷了他的不安使他说了出来。只是一愣,没有说话。他用手掐住我的双臂,想所有烂俗的戏码“如果你不想我离开,我就不走。”我呆呆地望着如瀑布般轰然而下的大雨。静默在我们之间流动。你尝试过拿出心脏放在牛肉盘里等着刀叉来袭击吗?此时我的心情正是如此。外面的雨如同滚烫的油滴一点一滴把我的心脏熔化得面目全非。
我伪装着我的冷静,避过他迫切的眼光,轻轻地说:“去吧!你去吧!”他愣了,紧皱着眉头,手上的力气像要把我的胳膊掐断:“为什们?你说啊!为什们?”面对他的层层质问,我瞥了他一眼,幽幽地说:“我们太年轻。如若你放弃了,将来会后悔的。”他放开我双臂,倚着墙壁,痛苦地挣扎着。我仿佛看到了此时的他与他帅气地对我说:“做我女朋友吧”的影像重叠,深深地刺痛我。
直到现在,或许宇还不知道,他妈妈在他告诉我的前一天找过我。她说:“可以感觉你是个很理性的女孩。希望你能为他好好想想。”那时候我其实是想打破我伪装的坚强,就像心理学说的,一个人如果外表坚强,那么他(她)是很容易破碎的。但我还是伪装着我的理性,把我的梦握成团放在宇的背包里。
当我把事情告诉铃时,铃说:“你真傻!”我该是明白的,或者我一直不明白。
现在的我搭上了高考的末班车,跌破所有人的眼镜,考进了一所大学。在大学校园里,看着微风拨动着浮云,我想起了宇,因为他曾说:我是宇宙,你是黑洞,你吞噬着我所有的不愉快。我一直想告诉他,我不想像黑洞,因为它同时也会吞噬掉你所有的愉快。而今的他,在艰苦地寻着他的梦,带着我的梦。青涩的果实往往没有表面那么可口,可是嚼完它,你会发现丝丝的甘甜。我现在从未感受到孤独,十八岁前的孤独,就像黑洞一直被宇宙包围着。我一直记着宇离开时对我说的一句话:等我。
好资讯
就像汽车碾过铺陈在马路上的稻谷时,疼的不仅仅是稻谷。十八岁的天空有着漂浮的白云,也有着飞机划过的尾翼。青涩的果实往往没有表面那么可口。
原以为会像许多在中国教育制度下平淡无奇地掠过高中,而后又潇洒地过上选修课必逃,必修课选逃的大学生活。
但一切的平静,在认识宇的那年夏天开始——
认识宇是源于偶然,但谁又知晓偶然不是源于自然。又或者假装深沉地说,有缘注定相见。宇是我们学校的家常。因为在众星拱月下,很荣幸,他不知不觉得到了校草的头衔。用他对我说的一句话说,就是“我简直是他们握在手中玩弄的布偶”。是有些偏激。不过,或许真有这么夸张,因为就连他在宿舍穿什么样的内裤都曾一度在校园里传得沸沸扬扬。人也许怕出名,不然高琨也不会让一次诺贝尔奖搞得鸡犬不宁;泰戈尔也不会因此远离芒果树下的天堂。
或许就像铃疯狂地以宇为偶像一样,我也在悄然中获得了学校的病毒。篮球场上,宇潇洒地身影尝尝是占据我的眼眶的。但那时我和宇也只是我从楼梯上,他从楼梯下的关系。是那几次的偶然使我们的关系改变。高二那年的夏天,命运似乎有意牵扯我们。打羽毛球时,我撞到他,他礼貌地笑了笑;打篮球时,篮球打到他,他礼貌地笑了笑;下楼梯时,撞到他,他一把扶住我,向我说了一句话“小姐,你和我有仇啊”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命运让他闯进我的生命?不过,我从未细想过高中生活没有他,是不是乏善可陈?
没有像有些恋人的一见钟情,我和宇也被编排到了慢热型的队伍中。宇常常说:“青春的年龄经不起时间的流逝”。他怕,我们的关系也会随着海水在净化器中淡化。我只能莞尔一笑。这一笑潜藏着太多的情绪,是无奈?是不以为然?是害怕?就像我无法回答一个孩子卡布奇诺为什么比一般的咖啡甜。
同宇交往的日子,我们重复着一般恋人的步骤。看电影,夜市。很多人常说90后的青春喜欢标新立异,殊不知90后的我们正喘息在“应该”中。
我或许是一种淡定的人,就像地快坍塌了,我还能在八楼上从容不迫地拿起手机说:“好,我马上下。”我不知道这样的性格是谁造就的,因为看过我爸妈为我中考的报名急的团团转的样子,你就会说:“你简直不是你爸妈生的。”也许吧!宇常常抱着我说:“你好轻。真怕你从我怀里逃走。‘其实不是这样的,因为,我也会怕。地板破裂了,碾碎的是我的肉体,而宇的离去将是撕裂我的心。
宇能荣登校草的宝座,绝不可能是无稽之谈。铃常说:“如果宇上快乐男声的话,岂会有陈楚生得第一的机会。宇是一个天之骄子。不仅篮球打得好,歌也唱得很好。他是星二代,他妈妈曾经是红遍大江南北的民歌歌手。许是良好的基因使他唱歌唱得很好。但对于像他这种通过音乐升学的学生来说,没有一番努力是不行的。星期一、星期三的下午我陪他练歌;星期二、星期五的下午我陪他打篮球;星期四的下午他陪我写作。像我这种平凡长相的女生,学校理科生的拖油瓶能够扯上宇简直就像是童话。可是并不是所有的灰姑娘都能如安徒生的陈述那样——过上幸福的生活。
我不知道我同意宇的离去是对这段感情的终点,还是给青春的遗憾,一种错觉,希冀他能带着他的梦想同我环游到南美洲的仙境瀑布。我曾说宇的离去会让我想脱了线的风筝,茫然无措。但真正遇到时,我还是坦然地去面对现实。
那段时间,宇常常是欲言又止,这让我很不习惯,对于一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来说,宇的行为让我感到不安。可是我不会主动去捅破这层纸,在他的心理准备还未完整的时候,我贸然地跨越会让他退缩。终于,在哪一个晚来的台风的日子,在艺术楼镂空的楼底,他说了:“我妈要我到巴黎。”我不知道是不是暴雨冲刷了他的不安使他说了出来。只是一愣,没有说话。他用手掐住我的双臂,想所有烂俗的戏码“如果你不想我离开,我就不走。”我呆呆地望着如瀑布般轰然而下的大雨。静默在我们之间流动。你尝试过拿出心脏放在牛肉盘里等着刀叉来袭击吗?此时我的心情正是如此。外面的雨如同滚烫的油滴一点一滴把我的心脏熔化得面目全非。
我伪装着我的冷静,避过他迫切的眼光,轻轻地说:“去吧!你去吧!”他愣了,紧皱着眉头,手上的力气像要把我的胳膊掐断:“为什们?你说啊!为什们?”面对他的层层质问,我瞥了他一眼,幽幽地说:“我们太年轻。如若你放弃了,将来会后悔的。”他放开我双臂,倚着墙壁,痛苦地挣扎着。我仿佛看到了此时的他与他帅气地对我说:“做我女朋友吧”的影像重叠,深深地刺痛我。
直到现在,或许宇还不知道,他妈妈在他告诉我的前一天找过我。她说:“可以感觉你是个很理性的女孩。希望你能为他好好想想。”那时候我其实是想打破我伪装的坚强,就像心理学说的,一个人如果外表坚强,那么他(她)是很容易破碎的。但我还是伪装着我的理性,把我的梦握成团放在宇的背包里。
当我把事情告诉铃时,铃说:“你真傻!”我该是明白的,或者我一直不明白。
现在的我搭上了高考的末班车,跌破所有人的眼镜,考进了一所大学。在大学校园里,看着微风拨动着浮云,我想起了宇,因为他曾说:我是宇宙,你是黑洞,你吞噬着我所有的不愉快。我一直想告诉他,我不想像黑洞,因为它同时也会吞噬掉你所有的愉快。而今的他,在艰苦地寻着他的梦,带着我的梦。青涩的果实往往没有表面那么可口,可是嚼完它,你会发现丝丝的甘甜。我现在从未感受到孤独,十八岁前的孤独,就像黑洞一直被宇宙包围着。我一直记着宇离开时对我说的一句话:等我。
好资讯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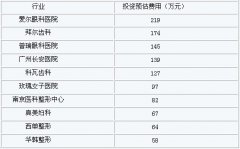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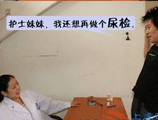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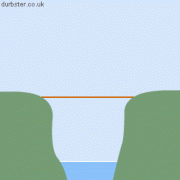
 闲来吧
闲来吧 娱乐视界
娱乐视界 生活社区
生活社区 情感驿站
情感驿站 网民生活
网民生活 旅游圈子
旅游圈子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