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篇
时间:2012-02-12 01:31来源: 作者:延安 点击:
次
2010年春天,我在钱塘江入海口的海宁市乡村住了一段时间,我了解到“钱江观潮” 的最佳位置就是我所住的这江段。能“钱江观潮” ,这是中国人很高贵,很文雅,很值得称道的幸事乐事,我就在钱塘江边,要不遊遊钱塘江,观观钱塘潮,会成为我一生憾事的。于是我在三月阳春,有淅淅春雨沥沥着的早晨,踏一电动自行车上了钱江大堤。
我上堤的位置是名扬海內外的钱江“回头潮”之地。这个地方叫盐仓,它是钱塘江真正的入海口,西边是钱塘江变窄了的江道,东边是辽阔的海洋面,因而就在这盐仓有一堵五、六百多米长的堤坝由北向南同钱塘江大堤连接,横在水中,挡住了海水,潮水到了这个地方,堤坝挡住了往西前进的方向,潮水就发怒般的冲撞堤坝,形成了“回头潮” ,“回头潮” 经过几次冲撞,最后力量渐弱,就乖乖的遁入了钱塘江道,同大潮汇合一起,顺钱塘江道逆水而上,这潮水会逆流而上上百里,最后终因争斗不过顺流而下的钱江水,而偃旗息鼓,结束“钱江水倒流” 的大自然奇观。
站在“回头潮” 大 堤上,看到江与海连成一片,连成一体,无边无际的海阔天空,海天一色,你不由的就自卑人在自然间的渺小。
从盐仓往东,往大海的方向去,大堤上吊着一只只的小魚船,鱼船很小,就是一只只小快艇。一根小碗口粗的钢管,斜插在大堤的钢管基座上,钢管很长,顶端有滑轮,是滑轮让小船升到空中的。漁民在岸边也撒有魚网,他们在早上冒着小雨在往岸上拉魚网,我撑着伞,观看魚民们收网,我看到一漁家姑娘连收拉了五、六只网,只收到几只半斤来重的小鱼我这时体会到餐桌上每条魚的来之不易,来之艰辛。这时有几只小船降滑到水面上,飞驰往江海的深处,他们开始了一天撒网捕魚的劳做。
从盐仓往东走,这里应该叫海了,海面宽的望不到边。大堤上边有弯弯曲曲的水泥路,骑着电动车,一只手撑着伞,沿江观景,确实有一番文兴、诗兴的趣味。
踏车上行十来公里,是更有名气的观潮点,这个地方叫盐官,这是个古镇。这相距二十里,一个镇叫盐官,一个镇叫盐仓,古时侯,食盐是官家管理的,这钱塘江入海处的滩塗,都是海水晒盐工场,因而设有盐官,住有盐官的地方就叫盐官镇,囤官盐的仓库叫盐仓镇。
在盐官的大堤上可以观赏到“一线潮” ,从大海湧过来的南潮和北潮,在盐官近百里的水面上汇和到一起,形成一条直直的白色浪花潮线,然后如千军万马,奔腾呼啸,势如破竹卷进钱塘江,顺者昌,逆者亡。
从盐官再往东走,有一个叫“碰头潮” 观赏位置,它距盐官又有一、二十里地,往东走我下了大堤,顺紧挨大堤的沿江公路骑车而行。这时毛毛的春雨住了,温暖的阳光轻柔的照抚着大地,照抚着盛开着油菜花的春日田野。田野里大面积盛开的油菜花把田野装扮的艳丽辉煌,油菜花是鲜黄色的,那黄色又奔放又张扬,把个春光中的大地映衬的温馨万千,芬芳万千;还有在这如画鲜黄景色中屹立的一大片、一大片农家小楼,小楼规模一样,都是三层高,楼墙是灰色的,屋顶是蓝色的小瓦,这些一律的灰墙蓝瓦建筑,呈现出很历史味的古色古香。
骑着车,看着路两边一边是海景,一边是野景,我庆幸自己真正欣赏到了现代文明的江南新景。我走的这条马路不宽,并且弯弯曲曲,马路两边长立着高高大大,又很有年代的杨槐树,杨槐树正盛开着槐花,弥漫着蜂蜜味的芳香,向前望去,马路两边的槐树似乎并到了一起,在我面前伸展开带子似的,蜿蜒曲折的,黑油油马路。
我骑车东行,一,是想赶着看十一点钟的“碰头潮” ,二,是想找到毛泽东在1957年阴历8月18日来钱塘江观潮赋诗的地方。我是从网上查到毛泽东观潮的地方是七星庙乡联玉村堤段。
在上午十点多钟,我终于看到路边有七星庙联玉村的路标,我停住车,问一坐在路边正在休息喝水的养路工人,问当年毛主席看潮的地方是在这里吗?那工人热情回答,是这一段,不过他老人家当年站的江堤不在了,他手指了南边的钢筋水泥大堤,说那老堤二十年前就被这新堤代替了。公路距大堤只几十米远,我停好电动车,迈步上了大堤,这里水面极宽,往南望不到边,我站在堤上,任海风吹着自己,脑海在想象领袖当年是何等心态在这里观潮赋诗。
据文献记载,1957年8月18主席来观潮,是保密的行动,他那时到南方视察住在杭州,至于为啥他会在这天早上想到观潮,也许是苏东坡那句:“八月十八潮,壮观天下无” 那两句诗吸引了他。他突然决定去海宁看潮,并且是秘密行动,不公开,不报道。
他们一行只几辆车,二十几人。他们路过盐仓,看大堤上看潮人已人山人海,又驱车到盐官,大堤上更是人多,主席为不扰民,就又让车子往东开,也就是在七星庙乡联玉村这堤段沒有观潮人,主席他们二十几人就上了这堤段,是在堤上等了一个多小时,才看到南潮从南来往西去,北潮从北来往西去,看“碰头潮” 还要往西几里地才会看到,而主席把看潮的好景点都让给他的百姓了。
就是看到这样的潮,诗人毛泽东也激发了诗兴,他看潮水滚滚西行,他想到了古人,想到了看潮的百姓,又想到了为江山南征北战的千军万马,当时解放军与盘距台湾的蒋军正在进行着炮击金门的炮战,还时有海战,间谍战,他盼望着台湾的解放,他似乎看到,他的百万大军战胜顽敌,结成宽阔的阵容,凱旋而归,从此马放南山,他的百姓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…………
诗人观着潮水,浮想联翩,诗人吟出了观潮七绝:
千里波涛滚滚来,
雪花飞向雨花台;
人山纷赞阵容阔,
铁马从容杀敌回。
毛主席的钱江观潮,消息封闭了三十七年,是在他死后的一九九二年,诗刊发表他这首观潮诗时,国人才知道他三十七年前曾去钱塘江观过潮,写过一首观潮诗。
不管从那方面说起,封闭毛主席的观潮消息,完全没有必要。我的看法是因这首观潮诗,毛主席诗词全集,五七年以后发表过很多回,但每次发表都没见这首观潮诗,这是与诗人不让发表有关联的,我猜想:是诗人对自己这首诗不滿意。都知道主席对自己的诗词要求很严格,要求标准很高,这首观潮诗从韵律,从大气,都表现不了主席诗词的风格,气势,要不不鸣,一鸣就要惊人,这是诗人一生的性格。该诗从各个方面都技压不了历代名人的观潮留笔。诗人是因为对自己这首诗的不滿意,以至这首诗他生前一直没有发表。
这个堤段沒有标示主席曾在此观过潮,他的观潮诗海宁人在县城明显位置建一碑亭,把该诗镌刻在碑上,让后人世代吟诵。
在上午十点四十五分,潮水来了,春天的潮很小,没有看到白浪滔天的南潮北潮,但看到整个海水在奔腾,在翻滚,在汹湧,在澎湃,似千军万马,吼叫着,浩浩荡荡,杀向钱塘江,海龙王与钱塘龙王展开大决战…………
潮水有十多分钟就过去了,看着远去的潮水,吟诵主席的观潮诗,我体会到诗人的心理感觉与常人不同,看这潮水汹湧奔腾,一般人都会想到千军万马是去出征上战场,而主席想的却是他的将军和士兵排成这样阵容是打了胜仗,东征胜利,凯旋归来。此景此情,主席对这段潮水的描写还是很到位的,不管是谁,站在这个位置看潮,能写出这样的诗句,还是只有我们的领袖。
在以后几天,我观赏了“一线潮” ,“回头潮” ,又了解了钱塘龙流传于民间的许多故事,我果然不虛此次钱江行,一生无憾矣!
2010年春于海宁
二 大 伯
对于二大伯,他给我留下最早的印象是农村吃人民公社大食堂饭那时侯,那时侯应该是一九五八年,我都七、八岁了,从这时侯以前,我记忆不清楚,记忆是模模糊糊的,所以有些事是听说的。
二大伯在年轻时长的很帅气,他中等的个头,白净的皮肤,额头上长有一个黃豆大小的肉瘤,老家人讲那叫“猴子” ,他那颗“猴子” 长的很有讲究,看相人说那颗“猴子” 有官相,可二大伯一辈子也没坐上官,连能吃“商品粮” 的国家普通干部也没混上。只是当过挣工分的生产大队副业组长,生产大队面粉厂厂长,生产小队队长。
从我记事记得他,二大伯穿衣很讲究,那是二大娘很会打扮丈夫,所以二大伯穿的衣服很干净很得体。老家上一辈人有句俗语:男人的穿戴是女人的脸,女人的裤腰带是男人的脸。
二大伯只有一个儿子,他抱养的女儿是老大,抱养女儿出嫁很早,她的女儿和我一般年纪。二大伯家人口少,因而生活负担不重,生活过的很滋润,二大娘很会做饭,同样都是炒萝卜絲,我母亲炒的就沒有二大娘炒的好吃。他们家的生活狀况,全村的人都很羨慕。
二大伯从小上过私塾,又在辛店上过完小。他是十六岁,我爷爷三十六岁患病突然去世后,就挑起了一个大家庭的重担。那时的全家有十几口人,有一个蒸酒作坊,还有长工、短工,奶奶是一个有一米五高,一个弱不禁风的农村女人,要掌管这么个大家庭,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奶奶自知领不起这个家,就把二大伯已定下亲的二大娘娶进门,协助二大伯管家。二大娘个子高有一米七多,年龄比二大伯大一岁,二大娘属于能说会道,很能理事的农家妇女。二大娘不识字,但她记性特别的好,我记得她会清楚的记得老戏全场的戏文和道白,并且是一字不差,这些戏有《穆桂英挂帅》,《陈三两爬堂》,《西厢记》……等十几场戏,夏夜乘凉,孩子们和母亲们会围她一圈,听她讲故事一样说戏。
二大伯有二大娘作帮手,奶奶把家里的大权全交给了他们俩,他们二人没负奶奶和全家人的厚望。二大伯他们亲姊妹五个,四男一女。二大伯当家后,他让体弱多病的父亲和八叔读书,身强力壮的三大伯和他在家蒸酒务农,姑姑是女孩,当然也是在家务农,跟着奶奶学纺花,织布,做鞋,绣花,做家务。
二大伯当家后最明显的成绩是供养了两个弟弟读书成材。父亲和八叔先是读私塾,完小是在辛店镇上读的,读完完小又都上县城上初中,初中上完父亲又上县办师范,八叔考上了郑州矿业技校。一九四九年新郑解放,父亲师范还沒完全毕业,就报名参加了新郑的教育工作,因为他是建国前参加了共产党的教育工作,也算是参加了革命,所以他六十岁退休时享受的是离休待遇。八叔是解放后毕业分配了工作,一直在武汉,冶金部勘探研究院工作。在我们老家农村,能一家有两个吃国家粮,拿国家工资的,享受国家干部待遇的,惟有我们一家,虽然二大伯二大娘沒沾上两个弟弟什么光,但他们供养成了两个国家干部是远近知名的。
现在二大伯过世有十七年了,父亲过世十年了,八叔还健在武汉,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。
二大伯在农村的生活并不苦,二大娘在世期间,是很会伺侯他的。他日子过的苦也就是七十五岁以后。那时侯二大娘已去世,生活料理都有他媳妇安排,跟媳妇生活,那当然是媳妇做什么吃什么。二大爷八十一岁那年他去世了,他这一辈子,父亲和八叔会接济他一些,但不经常。孙子、孙女在他需要帮助的时侯,由于自己还实力不济,他们也沒给于多大的帮助。虽然如此,二大伯的老年生活并沒缺吃缺穿,只是缺少零花钱,缺少几个老头子打麻将毛来角去的小本钱。
我记事起,二大伯对我就很好。他年轻时有一支“金龙” 牌的自来水笔,那支笔的笔杆是黑色的,大拇指粗的塑胶笔杆,吸墨水的皮囊很大,吸一囊墨水会用很长时间。他那支笔,我从七、八岁上学开始,就看在眼里,馋在心里了。二大伯在冬天穿黑色的制服棉袄,棉袄上四个兜,左胸上的小兜插着那支金笔,笔上的金黄色挂钩在阳光下很耀眼,很闪光。二大伯冬天还披件黑洋布棉大衣,那时人们把大衣叫“大敞” ,男人这样的穿戴在那年代很时尚,穿大衣,挂金笔,是刚解放那阵农村男人模仿下乡驻村的共产党干部而风行一时的,我儿时记忆,那时的村干部,农会干部都是这样打扮。而正式解放干部,他们穿的是黄色的军装,黄色的大衣,四个兜的上衣挂着金笔。
二大伯那支笔是金笔,所谓金也就是笔尖是金的,那支金笔写字很流利,下水也好,这就是好笔的主贵之处。我上学用的劣质笔最恨人之处是屙墨水,一屙一滩,辛苦一节课时间做的作业会一摊墨水毁于一旦。对那支笔我垂涎几年,几次向他提出要求,他不舍得给我,他说:“小孩子才上学用什么金笔?要是上到完小,这笔我才会送给你。”
我在村小学读书期间,我一直记着二大伯这句话。到我上辛店读完小,二大伯把他那支金笔真的送给了我。那支笔在我手上用有一年,因为笔太老了,二大伯说是他读完小时买的笔,少说用有二十多年了,这支老笔在我手上用坏了,因为没有笔尖换,只有扔掉了。
是在一九五九年,那时人们已开始饿肚子了。那是初春,天气还很寒冷,喝了生产队大食堂的稀粥后,二大伯让我跟他去岳庄一趟,我跟着他走了七、八里路到了岳庄,我们去的地方是人民公社的一个手工榨油作坊、二大伯和油坊的头头是朋友,那头头让我吃榨过油的芝麻麻糁饼,这榨过油的麻饼,是上田的好肥料,特别是种瓜,用麻饼追肥,结出的瓜会格外甜。可在那灾荒年,人们把糠吃了,树皮吃了,能吃上这麻饼,那就如吃肉一样的。
跟着二大伯吃了一晌的麻饼,晚上走时又吃了一碗油坊食堂里的手檊面条,那面条放上菠菜,放上芝麻油,放上辣椒,那吃着真叫个香,岁月过去五十多年了,一回忆起来,喉咙就湧上那芝麻油的香味。
二大伯还在辛店的面粉厂当过厂长,在粮食紧缺年代,能当面粉厂厂长,那是多少人都眼红的地方。他在当厂长的二年间,我在辛店上完小,吃住就在他那里。
一九八0年后,分田到户,由于我在生产队里一直当会计,农业活不全会做,特别是扬场。那时我这个家有五口人,有六、七亩地。麦子熟了,六,七亩小麦要打几个场。一大堆打了的小麦,麦糠、麦籽混在一起成一个大堆,二大伯知我不会扬场,就自家活干完后给我帮忙,这扬场就是他一把把教会我的。
凭心而论,对二大伯我没尽过多少孝顺,因为我的家境一直不太好,老是有外债,心有余力不足吧!
二大伯脾气很好,从我记事就沒见他同人打过架,同人吵架也很少。
二大伯的一生,平凡而没有辉煌,平平凡凡活了八十一年,最终又平平凡凡的离去,回归于人生平凡的泥土之中。
好资讯
我上堤的位置是名扬海內外的钱江“回头潮”之地。这个地方叫盐仓,它是钱塘江真正的入海口,西边是钱塘江变窄了的江道,东边是辽阔的海洋面,因而就在这盐仓有一堵五、六百多米长的堤坝由北向南同钱塘江大堤连接,横在水中,挡住了海水,潮水到了这个地方,堤坝挡住了往西前进的方向,潮水就发怒般的冲撞堤坝,形成了“回头潮” ,“回头潮” 经过几次冲撞,最后力量渐弱,就乖乖的遁入了钱塘江道,同大潮汇合一起,顺钱塘江道逆水而上,这潮水会逆流而上上百里,最后终因争斗不过顺流而下的钱江水,而偃旗息鼓,结束“钱江水倒流” 的大自然奇观。
站在“回头潮” 大 堤上,看到江与海连成一片,连成一体,无边无际的海阔天空,海天一色,你不由的就自卑人在自然间的渺小。
从盐仓往东,往大海的方向去,大堤上吊着一只只的小魚船,鱼船很小,就是一只只小快艇。一根小碗口粗的钢管,斜插在大堤的钢管基座上,钢管很长,顶端有滑轮,是滑轮让小船升到空中的。漁民在岸边也撒有魚网,他们在早上冒着小雨在往岸上拉魚网,我撑着伞,观看魚民们收网,我看到一漁家姑娘连收拉了五、六只网,只收到几只半斤来重的小鱼我这时体会到餐桌上每条魚的来之不易,来之艰辛。这时有几只小船降滑到水面上,飞驰往江海的深处,他们开始了一天撒网捕魚的劳做。
从盐仓往东走,这里应该叫海了,海面宽的望不到边。大堤上边有弯弯曲曲的水泥路,骑着电动车,一只手撑着伞,沿江观景,确实有一番文兴、诗兴的趣味。
踏车上行十来公里,是更有名气的观潮点,这个地方叫盐官,这是个古镇。这相距二十里,一个镇叫盐官,一个镇叫盐仓,古时侯,食盐是官家管理的,这钱塘江入海处的滩塗,都是海水晒盐工场,因而设有盐官,住有盐官的地方就叫盐官镇,囤官盐的仓库叫盐仓镇。
在盐官的大堤上可以观赏到“一线潮” ,从大海湧过来的南潮和北潮,在盐官近百里的水面上汇和到一起,形成一条直直的白色浪花潮线,然后如千军万马,奔腾呼啸,势如破竹卷进钱塘江,顺者昌,逆者亡。
从盐官再往东走,有一个叫“碰头潮” 观赏位置,它距盐官又有一、二十里地,往东走我下了大堤,顺紧挨大堤的沿江公路骑车而行。这时毛毛的春雨住了,温暖的阳光轻柔的照抚着大地,照抚着盛开着油菜花的春日田野。田野里大面积盛开的油菜花把田野装扮的艳丽辉煌,油菜花是鲜黄色的,那黄色又奔放又张扬,把个春光中的大地映衬的温馨万千,芬芳万千;还有在这如画鲜黄景色中屹立的一大片、一大片农家小楼,小楼规模一样,都是三层高,楼墙是灰色的,屋顶是蓝色的小瓦,这些一律的灰墙蓝瓦建筑,呈现出很历史味的古色古香。
骑着车,看着路两边一边是海景,一边是野景,我庆幸自己真正欣赏到了现代文明的江南新景。我走的这条马路不宽,并且弯弯曲曲,马路两边长立着高高大大,又很有年代的杨槐树,杨槐树正盛开着槐花,弥漫着蜂蜜味的芳香,向前望去,马路两边的槐树似乎并到了一起,在我面前伸展开带子似的,蜿蜒曲折的,黑油油马路。
我骑车东行,一,是想赶着看十一点钟的“碰头潮” ,二,是想找到毛泽东在1957年阴历8月18日来钱塘江观潮赋诗的地方。我是从网上查到毛泽东观潮的地方是七星庙乡联玉村堤段。
在上午十点多钟,我终于看到路边有七星庙联玉村的路标,我停住车,问一坐在路边正在休息喝水的养路工人,问当年毛主席看潮的地方是在这里吗?那工人热情回答,是这一段,不过他老人家当年站的江堤不在了,他手指了南边的钢筋水泥大堤,说那老堤二十年前就被这新堤代替了。公路距大堤只几十米远,我停好电动车,迈步上了大堤,这里水面极宽,往南望不到边,我站在堤上,任海风吹着自己,脑海在想象领袖当年是何等心态在这里观潮赋诗。
据文献记载,1957年8月18主席来观潮,是保密的行动,他那时到南方视察住在杭州,至于为啥他会在这天早上想到观潮,也许是苏东坡那句:“八月十八潮,壮观天下无” 那两句诗吸引了他。他突然决定去海宁看潮,并且是秘密行动,不公开,不报道。
他们一行只几辆车,二十几人。他们路过盐仓,看大堤上看潮人已人山人海,又驱车到盐官,大堤上更是人多,主席为不扰民,就又让车子往东开,也就是在七星庙乡联玉村这堤段沒有观潮人,主席他们二十几人就上了这堤段,是在堤上等了一个多小时,才看到南潮从南来往西去,北潮从北来往西去,看“碰头潮” 还要往西几里地才会看到,而主席把看潮的好景点都让给他的百姓了。
就是看到这样的潮,诗人毛泽东也激发了诗兴,他看潮水滚滚西行,他想到了古人,想到了看潮的百姓,又想到了为江山南征北战的千军万马,当时解放军与盘距台湾的蒋军正在进行着炮击金门的炮战,还时有海战,间谍战,他盼望着台湾的解放,他似乎看到,他的百万大军战胜顽敌,结成宽阔的阵容,凱旋而归,从此马放南山,他的百姓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…………
诗人观着潮水,浮想联翩,诗人吟出了观潮七绝:
千里波涛滚滚来,
雪花飞向雨花台;
人山纷赞阵容阔,
铁马从容杀敌回。
毛主席的钱江观潮,消息封闭了三十七年,是在他死后的一九九二年,诗刊发表他这首观潮诗时,国人才知道他三十七年前曾去钱塘江观过潮,写过一首观潮诗。
不管从那方面说起,封闭毛主席的观潮消息,完全没有必要。我的看法是因这首观潮诗,毛主席诗词全集,五七年以后发表过很多回,但每次发表都没见这首观潮诗,这是与诗人不让发表有关联的,我猜想:是诗人对自己这首诗不滿意。都知道主席对自己的诗词要求很严格,要求标准很高,这首观潮诗从韵律,从大气,都表现不了主席诗词的风格,气势,要不不鸣,一鸣就要惊人,这是诗人一生的性格。该诗从各个方面都技压不了历代名人的观潮留笔。诗人是因为对自己这首诗的不滿意,以至这首诗他生前一直没有发表。
这个堤段沒有标示主席曾在此观过潮,他的观潮诗海宁人在县城明显位置建一碑亭,把该诗镌刻在碑上,让后人世代吟诵。
在上午十点四十五分,潮水来了,春天的潮很小,没有看到白浪滔天的南潮北潮,但看到整个海水在奔腾,在翻滚,在汹湧,在澎湃,似千军万马,吼叫着,浩浩荡荡,杀向钱塘江,海龙王与钱塘龙王展开大决战…………
潮水有十多分钟就过去了,看着远去的潮水,吟诵主席的观潮诗,我体会到诗人的心理感觉与常人不同,看这潮水汹湧奔腾,一般人都会想到千军万马是去出征上战场,而主席想的却是他的将军和士兵排成这样阵容是打了胜仗,东征胜利,凯旋归来。此景此情,主席对这段潮水的描写还是很到位的,不管是谁,站在这个位置看潮,能写出这样的诗句,还是只有我们的领袖。
在以后几天,我观赏了“一线潮” ,“回头潮” ,又了解了钱塘龙流传于民间的许多故事,我果然不虛此次钱江行,一生无憾矣!
2010年春于海宁
二 大 伯
对于二大伯,他给我留下最早的印象是农村吃人民公社大食堂饭那时侯,那时侯应该是一九五八年,我都七、八岁了,从这时侯以前,我记忆不清楚,记忆是模模糊糊的,所以有些事是听说的。
二大伯在年轻时长的很帅气,他中等的个头,白净的皮肤,额头上长有一个黃豆大小的肉瘤,老家人讲那叫“猴子” ,他那颗“猴子” 长的很有讲究,看相人说那颗“猴子” 有官相,可二大伯一辈子也没坐上官,连能吃“商品粮” 的国家普通干部也没混上。只是当过挣工分的生产大队副业组长,生产大队面粉厂厂长,生产小队队长。
从我记事记得他,二大伯穿衣很讲究,那是二大娘很会打扮丈夫,所以二大伯穿的衣服很干净很得体。老家上一辈人有句俗语:男人的穿戴是女人的脸,女人的裤腰带是男人的脸。
二大伯只有一个儿子,他抱养的女儿是老大,抱养女儿出嫁很早,她的女儿和我一般年纪。二大伯家人口少,因而生活负担不重,生活过的很滋润,二大娘很会做饭,同样都是炒萝卜絲,我母亲炒的就沒有二大娘炒的好吃。他们家的生活狀况,全村的人都很羨慕。
二大伯从小上过私塾,又在辛店上过完小。他是十六岁,我爷爷三十六岁患病突然去世后,就挑起了一个大家庭的重担。那时的全家有十几口人,有一个蒸酒作坊,还有长工、短工,奶奶是一个有一米五高,一个弱不禁风的农村女人,要掌管这么个大家庭,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奶奶自知领不起这个家,就把二大伯已定下亲的二大娘娶进门,协助二大伯管家。二大娘个子高有一米七多,年龄比二大伯大一岁,二大娘属于能说会道,很能理事的农家妇女。二大娘不识字,但她记性特别的好,我记得她会清楚的记得老戏全场的戏文和道白,并且是一字不差,这些戏有《穆桂英挂帅》,《陈三两爬堂》,《西厢记》……等十几场戏,夏夜乘凉,孩子们和母亲们会围她一圈,听她讲故事一样说戏。
二大伯有二大娘作帮手,奶奶把家里的大权全交给了他们俩,他们二人没负奶奶和全家人的厚望。二大伯他们亲姊妹五个,四男一女。二大伯当家后,他让体弱多病的父亲和八叔读书,身强力壮的三大伯和他在家蒸酒务农,姑姑是女孩,当然也是在家务农,跟着奶奶学纺花,织布,做鞋,绣花,做家务。
二大伯当家后最明显的成绩是供养了两个弟弟读书成材。父亲和八叔先是读私塾,完小是在辛店镇上读的,读完完小又都上县城上初中,初中上完父亲又上县办师范,八叔考上了郑州矿业技校。一九四九年新郑解放,父亲师范还沒完全毕业,就报名参加了新郑的教育工作,因为他是建国前参加了共产党的教育工作,也算是参加了革命,所以他六十岁退休时享受的是离休待遇。八叔是解放后毕业分配了工作,一直在武汉,冶金部勘探研究院工作。在我们老家农村,能一家有两个吃国家粮,拿国家工资的,享受国家干部待遇的,惟有我们一家,虽然二大伯二大娘沒沾上两个弟弟什么光,但他们供养成了两个国家干部是远近知名的。
现在二大伯过世有十七年了,父亲过世十年了,八叔还健在武汉,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。
二大伯在农村的生活并不苦,二大娘在世期间,是很会伺侯他的。他日子过的苦也就是七十五岁以后。那时侯二大娘已去世,生活料理都有他媳妇安排,跟媳妇生活,那当然是媳妇做什么吃什么。二大爷八十一岁那年他去世了,他这一辈子,父亲和八叔会接济他一些,但不经常。孙子、孙女在他需要帮助的时侯,由于自己还实力不济,他们也沒给于多大的帮助。虽然如此,二大伯的老年生活并沒缺吃缺穿,只是缺少零花钱,缺少几个老头子打麻将毛来角去的小本钱。
我记事起,二大伯对我就很好。他年轻时有一支“金龙” 牌的自来水笔,那支笔的笔杆是黑色的,大拇指粗的塑胶笔杆,吸墨水的皮囊很大,吸一囊墨水会用很长时间。他那支笔,我从七、八岁上学开始,就看在眼里,馋在心里了。二大伯在冬天穿黑色的制服棉袄,棉袄上四个兜,左胸上的小兜插着那支金笔,笔上的金黄色挂钩在阳光下很耀眼,很闪光。二大伯冬天还披件黑洋布棉大衣,那时人们把大衣叫“大敞” ,男人这样的穿戴在那年代很时尚,穿大衣,挂金笔,是刚解放那阵农村男人模仿下乡驻村的共产党干部而风行一时的,我儿时记忆,那时的村干部,农会干部都是这样打扮。而正式解放干部,他们穿的是黄色的军装,黄色的大衣,四个兜的上衣挂着金笔。
二大伯那支笔是金笔,所谓金也就是笔尖是金的,那支金笔写字很流利,下水也好,这就是好笔的主贵之处。我上学用的劣质笔最恨人之处是屙墨水,一屙一滩,辛苦一节课时间做的作业会一摊墨水毁于一旦。对那支笔我垂涎几年,几次向他提出要求,他不舍得给我,他说:“小孩子才上学用什么金笔?要是上到完小,这笔我才会送给你。”
我在村小学读书期间,我一直记着二大伯这句话。到我上辛店读完小,二大伯把他那支金笔真的送给了我。那支笔在我手上用有一年,因为笔太老了,二大伯说是他读完小时买的笔,少说用有二十多年了,这支老笔在我手上用坏了,因为没有笔尖换,只有扔掉了。
是在一九五九年,那时人们已开始饿肚子了。那是初春,天气还很寒冷,喝了生产队大食堂的稀粥后,二大伯让我跟他去岳庄一趟,我跟着他走了七、八里路到了岳庄,我们去的地方是人民公社的一个手工榨油作坊、二大伯和油坊的头头是朋友,那头头让我吃榨过油的芝麻麻糁饼,这榨过油的麻饼,是上田的好肥料,特别是种瓜,用麻饼追肥,结出的瓜会格外甜。可在那灾荒年,人们把糠吃了,树皮吃了,能吃上这麻饼,那就如吃肉一样的。
跟着二大伯吃了一晌的麻饼,晚上走时又吃了一碗油坊食堂里的手檊面条,那面条放上菠菜,放上芝麻油,放上辣椒,那吃着真叫个香,岁月过去五十多年了,一回忆起来,喉咙就湧上那芝麻油的香味。
二大伯还在辛店的面粉厂当过厂长,在粮食紧缺年代,能当面粉厂厂长,那是多少人都眼红的地方。他在当厂长的二年间,我在辛店上完小,吃住就在他那里。
一九八0年后,分田到户,由于我在生产队里一直当会计,农业活不全会做,特别是扬场。那时我这个家有五口人,有六、七亩地。麦子熟了,六,七亩小麦要打几个场。一大堆打了的小麦,麦糠、麦籽混在一起成一个大堆,二大伯知我不会扬场,就自家活干完后给我帮忙,这扬场就是他一把把教会我的。
凭心而论,对二大伯我没尽过多少孝顺,因为我的家境一直不太好,老是有外债,心有余力不足吧!
二大伯脾气很好,从我记事就沒见他同人打过架,同人吵架也很少。
二大伯的一生,平凡而没有辉煌,平平凡凡活了八十一年,最终又平平凡凡的离去,回归于人生平凡的泥土之中。
好资讯
- 上一篇:无 题(六十最高境界漫谈)
- 下一篇:我曾是你的眼
热点资讯
- 预约想念
总喜欢在沉寂的黑夜静想,亦喜欢在黄昏写一些文字。暮色四合,我习惯在某个地方发呆,...
- 朝花夕拾《心语》
让旧时光轻盈,让心情放飞,在这个秋日,我是如此灿烂。。。...
- 一场突袭的忧伤
无意中上网,空间里看到你和一个女孩出去玩,站在一起的照片。不知道,心里竟是如此的...
- 一个人的命运决定于晚上8点到10
一个人的成就,不是以金钱衡量,而是一生中,你善待过多少人。...
- 我的爱情,月老你牵了红线吗?
上帝请你赐予我一个真诚的爱情,如果实现,我将会用心的去爱。如果真的有一个女的,能...
- 青春的肩膀,我的高度
...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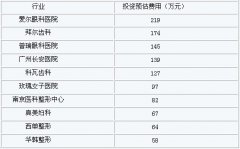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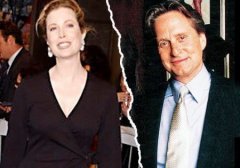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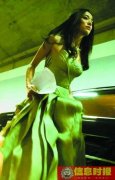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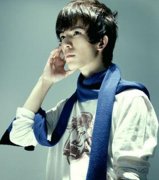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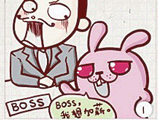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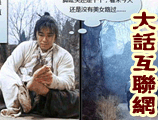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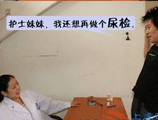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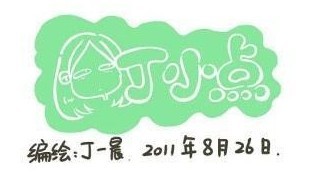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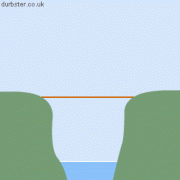
 闲来吧
闲来吧 娱乐视界
娱乐视界 生活社区
生活社区 情感驿站
情感驿站 网民生活
网民生活 旅游圈子
旅游圈子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