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蓑烟雨任平生
十月,秋高气爽。我虔诚地礼拜了庄严、肃穆的乐山大佛之后,转身来到被陆游称为“千载诗书城”的眉山市,拜谒我心中的大佛:苏东坡先生。
在三苏祠里,我站在先生高大、雄伟的塑像前,低头默哀三分钟,然后下拜,行三跪九叩大礼。站起身,我看到先生面带微笑地望着我,似乎有话要说。我连忙说:“先生,我是从黄州来的,特来看望您。您还记得黄州吗?”只见先生目视远方,似乎要透过千里,越过千年,寻找黄州的回忆。
黄州,对先生风雨一生,是十分重要的,他给自己的一生作总结时说:“心如槁灰之木,身似不系之舟,问汝平生事业,黄州、惠州、儋州。”把黄州排在第一位。
宋朝,是历代文人向往的时代,是一个文化繁盛的时代,也是历史上对文化最宽容的时代。然而,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苏轼,一个光照千秋的文学天才,一个狷直、耿介的文人,竟无端因文字罹祸,受尽屈辱,几临被杀的境地!
元丰二年(1079年),先生因“文字毁谤君相”一个“莫须有”罪名,被捕下狱(史称“乌台诗案”),坐牢103天。先生罹祸后,他曾为官的杭州父老百姓公开做解厄道场,求告神明保佑;朝中一些正直的大臣如张方平、范缜、吴充等纷纷为先生鸣不平,政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仗义执言,后有太皇太后出面保护,才免去死罪,贬谪黄州。
从此,黄州载入了光辉的中国文学史册。
刚到黄州,先生暂住在定惠寺院。此时家眷还未到达,他和僧人一同吃饭,饭后常在林间散步,颇为闲适。家眷到达之后,他的经济陷入艰难,日子要如何过,他还没想好。他的两个小儿子适和过,一个十二岁,一个十岁。由于太守的礼遇,他们住在临皋亭(驿亭,接待过往官员的地方。此地后来因先生而得名)。先生曾给一个朋友描述过临皋亭:“寓居去江无十步,风涛烟雨,晓夕百变。江南诸山在几席,此幸未始有也。”
我想,临皋亭并不见得真是那么美吧,风光之美一半在自然,另一半则在观赏风景之人。先生是天才,对美有着极高鉴赏力,能见到感到别人即便在天堂也见不到感不到的美;二则大约怕那些朋友为他担心,故意把环境说得美好,宽慰他们;三则借想象中的美景抚慰自己那颗受伤的心灵。
我们现在无法知道当时黄州的情境,也不知道先生当年居住的确切地方。闲暇中,我常在黄州街头彳亍,想寻找先生当年足迹,却总也找不到。但我知道,先生当年的环境是十分艰难的,生活也是十分凄苦的,那些优美的诗文,只不过是他在生活的挣扎中的精神的超越。
在先生的一些书信中,还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生活情境。他在给李端叔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:“得罪以来,深自闭塞,扁舟草履,放浪山水间,与樵渔杂处,往往为醉人所推骂,辄自喜渐不为人识。平生亲友,无一字见及,有书与之亦不答,自幸庶几免矣。”
世态炎凉,朋友绝迹。在寂寞、孤独、伤感中,又寻些自我安慰。培根说:“顺境需要人的节制,逆境需要人的忍耐;顺境中最易暴露恶行,逆境中最能彰显美德。”逆境中的苏轼,更彰显其美德、张扬其人格魅力。
不久,身边便有了不少新朋友,徐太守热诚相待,常以酒宴相邀;武昌(今鄂州)朱太守也常送酒食给他。在雨天,先生睡到很迟才起床;黄昏时,在起伏不平的东山麓漫游,在庙宇、私人庭园、树阴掩蔽的溪流等处探胜寻幽。江边有风光秀丽的龙王山,江对岸就是著名的西山风景区,有时朋友来访,就一同到江两岸的山里游玩。
先生的生活表面是闲适、平静的,心里却十分苦闷。他的官职是黄州团练副使(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),只是一个闲职,实际上停止了他的一切工作,大约还有依附权贵的奴才颁发的“只准值班、看书、闭门思过”的指令,对先生进行了种种无耻的人身限制。因此,他在写给官居参政谏议执事(副宰相)的章子厚的信中说:“黄州僻陋多雨,气象昏昏也。鱼稻薪炭颇贱,甚与穷者相宜……现寓僧舍,布衣蔬饮,随僧一餐,差为简便……初到一见太守。自余杜门不出,闲居未免看书,惟佛经以遣日,不复近笔砚矣。”
这封信,与其说是写给章子厚的,不如说是写给朝庭的公开信。信中着重告诉朝庭官员:1、黄州环境恶劣;2、我住在庙里,很穷困;3、只是刚来时与太守见过一次面,此后没有任何人来看我;4、每天只是“看书、闭门思过”,5、没有写文章(也没有网可上)。这下你们放心了吧!
苏轼不仅“闭门思过”,还要向权贵们表示道歉、忏悔。他在给章子厚的信中还沉痛地忏悔道:“今在囹圄中,追悔无路,谓必死矣。不意圣主宽大,复遣视息人间。若不改者,某真非人也……某昔年粗亦受知于圣主,使稍循理安分,岂有今日?追思所犯,真无义理,与病狂之人,蹈河入海者无异。”
先生这样才情卓绝、性情孤傲、品行高洁的人,面对权势、邪恶,竟如此作贱自己,作出如此深刻地痛悔、道歉,读来让人心颤。我们不能因此责备先生屈服权势,低下高贵的头,要知道,在生命与人格的尊严面前,哪个更重要?别说是先生这样的文人,就连豪气冲天的岳飞,在狱中面对小小狱率,也俯首低眉,浑身颤栗啊。塞奈卡说:“一个人只有同时具备脆弱的人性和不可战胜的神性,才算得上真正的伟大。”中国传统提倡宁折不弯,我则认为:大丈夫能屈能伸,是好汉宁弯不折。面对权势,面对淫威,可以低头,可以弯腰,但决不能折断脊梁骨,这,就是文人。因此,批判、忏悔、道歉,丝毫无损于伟人们人格的光辉,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言:“批判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剥夺被批判者的人格尊严,但奇怪的是,中国近代以来真正具有人格尊严的名人,几乎没有一个未遭受过批判。未曾遭受过批判的名人,反而都黯然失色,被人忘却。批判像一块粗砺的抹布,往往使擦拭的对象越加清晰亮堂。”
先生在黄州的生活的确是困难的。他在给秦少游的信里说:“初到黄州,凛人既绝,人口不少,私甚忧之。但痛自节省,日用不得百五十(等于美金一角五分)。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,断为三十块,挂屋梁上。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,即藏去。钱仍以大竹筒别贮,用不尽以待宾客。此贾耘老(贾收)法也。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。至时别作经画,水到渠成,不须预虑。以此胸中都无一事。”
苏轼的黄州生活是凄苦的,心情是郁闷的,精神是孤独的,思想更是矛盾的。一首《卜算子》道尽了他那份难言的孤寂:
缺月挂疏桐,漏断人初静。谁见幽人独往来?缥缈孤鸿影。
惊起却回头,有恨无人省。拣尽寒枝不肯栖,寂寞沙洲冷。
一个热爱祖国,热爱人民,热爱事业的人,被权贵摆弄,无所施为;一个才情闪耀、品行高洁、性格潇洒的高傲灵魂,被奴才禁锢,只能闭门读书、思过……这该是多么痛苦的事啊!有人说得很好听,什么“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”;还有更动听的,叫做“居庙堂之高,则忧其民;处江湖之远,则忧其君”,这些说法的确是很漂亮,但却都是虚伪的废话。古往今来,求达必先变节,成为巴儿狗,成为权贵掌中的玩物,这样自保都难,又谈何兼济?穷善其身倒不错,可这是无奈,穷意味着失去恶的能力,想恶也恶不起来,不善也得善。至于忧民忧君,更是一厢情愿,自作多情。居庙堂,必沦为奴才;处江湖,则成遗世孑民,还哪里轮得着你忧这忧那的?
既不用你忧民,也不用自作多情去忧君,还是干点实事吧。在友人马梦德的帮助下,先生请得东坡荒地,以“东坡”自名,开始过起了开荒种地,自耕自食的农夫生活。《东坡八首》就表明他认真的态度,真诚的心愿,真实的疾苦和感受,坦坦荡荡,堂堂正正:“良农惜地力,幸此十年荒。柔拓未及成,一麦庶可望。投种未逾月,覆块已苍苍。农夫告我言,勿使苗叶昌。君欲福饼饵,要须纵牛羊。再拜谢苦言,得饱不敢忘。”(《东坡八首其四》)。
从此,世界上有了一个伟大而响彻千年的名字:苏东坡。
培根说:“如果奇迹的意义在于超越天命,那么,它通常就出现在逆境之中……美德就好比名贵的香料,愈是燃烧,愈是碾压,其香却愈为浓烈。”
逆境中,先生的田园生活是恬适而丰富的。农舍后面是远景亭,下面乡野景色,一览无遗。他的西邻姓古,有一片竹林,枝叶茂密,人行其中,不见天日。先生常在此浓阴之中,消磨长夏,并寻找干而平滑的笋壳,供太太做鞋衬里之用。
还有一大帮邻人和朋友:潘酒监、郭药师、庞大夫……还有一个说话大嗓门跋扈霸道的婆娘,常和丈夫吵嘴,夜里像猪一般嗥叫。
他在札记里写道:“东坡居士酒醉饭饱,倚于几上,白云左绕,青江右回,重门洞开,林峦岔入。当是时,若有思而无所思,以受万物之备。惭愧,惭愧。”一封写给朋友范镇儿子的信里说:“临皋亭下十数步,便是大江,其半是峨眉雪水。吾饮食沐浴皆取焉,何必归乡哉?江水风月本无常主,闲者便是主人。” 在著名的《前赤壁赋》中,先生进一步发挥:“且夫天地之间,物各有主。苟非吾之所有,虽一毫而莫取。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,取之无禁,用之不竭,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,而吾与子之所共适。”
先生的黄州生活,本凄苦、寂寥,多亏朋友们给他几许热闹;但真正给他抚慰、熨平他心头创伤的,是他生活、心灵的伴侣——侍妾王朝云。
先生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小诗,几乎人人能诵。此诗虽为描写西湖旖旎风光,而实际上是先生初遇王朝云时为之心动的感受:
水光潋滟晴方好,山色空蒙雨亦奇;
欲把西湖比西子,浓装淡抹总相宜。
王朝云,字子霞,钱塘人,因家境清寒,自幼沦落在歌舞班中。她天生丽质,聪颖灵慧,能歌善舞,虽混迹烟尘之中,却独具一种清新洁雅的气质。神宗熙宁四年,先生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被贬为杭州通判,一日,他与几位文友同游西湖,宴饮时招来王朝云所在的歌舞班助兴,悠扬的丝竹声中,数名舞女浓妆艳抹,长袖徐舒,轻盈曼舞,而舞在中央的王朝云又以其艳丽的姿色和高超的舞技,特别引人注目。舞罢,众舞女入座侍酒,王朝云恰转到苏轼身边,此时的王朝云又换了另一种装束:洗净浓装,黛眉轻扫,朱唇微点,一身素净衣裙,清丽淡雅,楚楚可人,别有一番韵致,仿佛一股空谷幽兰的清香,沁入先生因世事变迁而黯淡的心。当时,本是丽阳普照,波光潋滟的西湖,由于天气突变,阴云敝日,山水迷蒙,成了另一种景色。湖山佳人,相映成趣,先生灵感顿至,挥毫写下了传颂千古的描写西湖佳句。此后,先生对王朝云备极宠爱,收为侍女。到黄州,正式纳为妾。
王朝云不仅温婉贤淑,更善解先生的心意。一次,先生退朝回家,饭后在庭院中散步,突然指着自己的腹部问身边的侍妾:“你们有谁知道我这里面有些什么?”一侍女答道:“您腹中都是文章。”先生不以为然。另一侍女说:“满腹都是见识。”先生也摇摇头,到了王朝云,她微笑道:“大学士一肚皮的不合时宜。”先生闻言,捧腹大笑,赞道:“知我者,唯有朝云也。”
正是这种“不合时宜”,使先生饱受流离之苦;也正是这“不合时宜”的独立人格,才有照耀千秋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魅力。
杭州四年,之后又官迁密州、徐州、湖州,颠沛流离,王朝云始终紧紧相随,无怨无悔。在黄州,王朝云布衣荆钗,与先生患难与共,悉心调理先生的生活起居。她用黄州廉价的肥猪肉,微火慢烘,烘出香糯滑软,肥而不腻的肉块,作为先生常食的佐餐妙品,这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“东坡肉。”元丰六年,先生46岁,王朝云生下一子。老年得子,先生十分高兴,取名遂礼,并写诗一首:
人皆养子望聪明,我被聪明误一生;
唯愿孩儿愚且鲁,无灾无难到公卿。
先生想到从昔日的名躁京华,到而今的“自渐不为人识”,灾难重重,流离失所,都是因为聪明所致。他终于悟到,只有“愚且鲁”,才能无灾无难;只有“愚且鲁”,才能青云直上到公卿。
后,先生年近花甲时再次被贬往南蛮之地的惠州,眼看运势转下,难得再有起复之望,身边众多的侍儿姬妾都陆续散去,只有王朝云始终如一,伴随着先生长途跋涉,翻山越岭到惠州。后朝云病死惠州,年仅三十四岁。先生将她葬在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,并筑六如亭以纪念,亭柱上镌有一副楹联,是先生亲自手书:
不合时宜,惟有朝云能识我;
独弹古调,每逢暮雨倍思卿。
在黄州,先生对世态炎凉的体验更深,还有着“我今飘泊等鸿雁,江南江北无常栖”的飘零之痛。幽独的生活中,先生常常在僧房里面壁静坐,并不是真的“闭门思过”,而是进入一个更高深的境界。《金刚经》、《华严经》、《圆觉经》、《般若心经》、《清静经》、《六祖坛经》、《传灯录》……无所不读,经过多年宦海沉浮,而今又在佛教义理的感化下,先生了悟了万事本空的道理,对禅理、人生的理解也达到了一种适意自由的大自在境界,加之其本身性格开朗旷达,在经历了人生大难后心态变得平和,“世路如今已贯,此心到处悠然”。
困境,可以使人沉沦,也可以使人飞升。经过“乌台诗案”的冶炼,又经过黄州的孕育,一个新的“苏东坡”矗立在世人面前,以前后《赤壁赋》、《赤壁怀古》为代表的一大批千古杰作喷薄而出,像雨后彩虹,照耀了历史的天空:
大江东去,浪淘尽、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,人道是、三国周郎赤壁。乱石穿空,惊涛拍岸,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画,一时多少豪杰。
遥想公瑾当年,小乔初嫁了,雄姿英发。羽扇纶巾,谈笑间、樯虏灰飞烟灭。故国神游,多情应笑我,早生华发。人生如梦,一樽还酹江月。
浩浩历史长河,皇帝、高官有多少?而苏东坡只有一个。“东坡”之名,是因黄州而取;坡公的成就,是因黄州而成。可以说,没有黄州,就没有苏东坡。是当年那批权贵和龌龊小人,成就了东坡,是东坡成就了黄州,是东坡黄州成就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!当我们怀念坡公,品赏坡公千古杰作时,真应该好好感谢那批权贵和龌龊小人!
周国平说:“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。安静,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。丰富,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。”远离了权贵的肮脏,远离了政治的染缸,坡公的生活是丰富而安静的,才有黄州东坡的清新隽永。东坡黄州诗文的缕缕清气也从黄州那纯净山水飘向神州大地,直到今天,直到永远……
经过了黄州的风雨岁月,坡公胸襟开阔,眼界无限,一个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旷达巨人站立在世人面前。哪怕前面仍然风狂雨骤,我自从容淡定,波澜不惊,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。
《定风波》:
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料峭春风吹酒醒,微冷,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
好资讯
- 上一篇:窗外
- 下一篇:爱上你,也许只因你我双眼相交的一瞬间
热点资讯
- 四季悲歌
春鸟鸣, 惊醒甜甜美梦, 穿上绿衣, 重新接受残酷现实, 幽幽轮回中, 麻木了谁...
- 就这样慢慢走远
离昨天远了,日子渐渐清晰。这成长路上的期翼,我拾起一块,深埋大地。一直...
- 藕花深处
一壶浊酒,一漫青沙,我在长江之南点燃九盏孔明灯,照影你最初的幻美和纯洁。那个人纵...
- 冰雪融化,我初回
一场寒冷将过往覆盖,却演绎另一场开端。冰雪化水,带着每一个细节沾满的一诺千金...
- 我是个寂寞的孩子
我手里握着大把大把的寂寞,它们以时光的形式从我手中溜走,溜走又悄无声息的回来。我...
- 我的等待
我的等待 一直不明白, 我,为了什么活着? 冷漠的看着世界, 微笑着看那些小丑们, ...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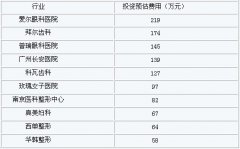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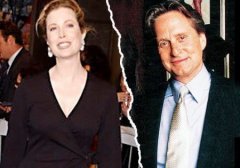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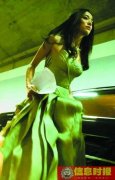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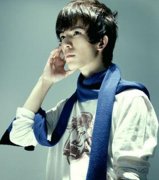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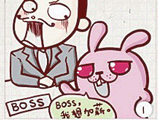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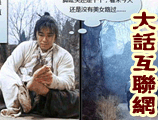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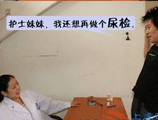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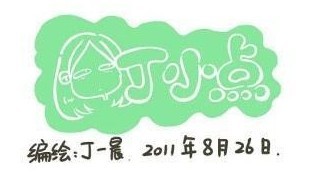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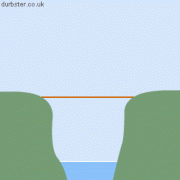
 闲来吧
闲来吧 娱乐视界
娱乐视界 生活社区
生活社区 情感驿站
情感驿站 网民生活
网民生活 旅游圈子
旅游圈子




